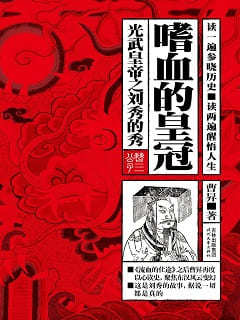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自序
- [ 免費 ] 第壹章 少年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洛麗塔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太學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從中興到末路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新帝王莽
- [ 免費 ] 第六章 地皇二年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地皇三年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十月革命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沘水大捷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更始皇帝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鎮國之寶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昆陽大戰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手足之斷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新朝覆滅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潛龍勿用
- [ 免費 ] 第壹章 飛龍在天
- [ 免費 ] 第二章 走出冀州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絕地反擊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河北女婿
- [ 免費 ] 第五章 短命君王
- [ 免費 ] 第六章 銅馬皇帝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天子輩出
- [ 免費 ] 第八章 西京東都
- [ 免費 ] 第九章 少年鄧奉的煩惱 ...
- [ 免費 ] 第十章 長安之亂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後院起火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戰神哀歌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既得隴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復望蜀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尾聲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壹章 飛龍在天
2018-10-1 15:16
【No.1 出洛陽記】
這段禱詞寫在下面:
“我們在天上的父,我們日用的飲食,今日賜給我們。免我們的債,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,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,全是妳的,直到永遠。”
漢更始元年(公元二十三年)十月,洛陽。劉秀的處境相當不妙,他的債無法免去,他遇見的試探無處不在,而又有誰能救他脫離兇惡?
劉秀所能做的,似乎只剩下祈禱而已。
洛陽城中,血光正在醞釀,朱鮪等人已經為他伏下刀槍。這不僅是他的預感,更有劉賜的提醒為證。倘若他只想保命,事情倒也簡單,大不了改換姓名,亡命他鄉,萬人海中壹身藏,從此山林中多了壹位蕭索的隱士,又或者村莊裏多了壹位卑微的農夫,而世間不再有劉秀劉文叔。然而,像這樣壹躲,他雖然能活下去,卻無異於已經死了,他的仇恨、雄心,包括與陰麗華的婚姻,隨著這壹躲,將從此無聲飲恨,化為無人過問的小徑,荒草長滿,抱憾殘生。
因此,他不僅要活下去,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活下去。他的確要遠離洛陽,躲離朱鮪等人的魔掌,但絕不能以逃亡的方式,而必須以漢朝官員的身份堂堂正正地離開,外放到壹個天高皇帝遠、可以積攢實力的地方。
而就漢朝更始政府而言,盡管王莽的新朝已經覆滅,但天下並不太平,全國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州郡並未正式納入帝國的版圖,因此也就需要大量的外放官員,前往這些州郡進行安撫招降。
更始政府中的當權派——出身綠林軍和南陽豪傑的那些高級將領們,沒有人願意外放,他們明白,很快就要大賞功臣,瓜分勝利果實,在此關鍵時刻,他們都爭著要留在皇帝劉玄身邊,盯緊自己該得的那份封賞。因此,安撫州郡的任務,很自然地便落在了壹批低級官吏的頭上。
在眾多尚未歸順朝廷的州郡之中,河北地區是壹個例外。所謂河北,在當時泛指黃河以北,地域涵蓋今之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地。其余州郡,即使派壹個不得力的低級官吏去,也可以傳檄而定。然而在河北,局面卻遠非如此輕易。
河北地區乃戰國時代的燕趙故地,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,民風強悍,野心家眾多,而此時的河北,更是流民武裝滋盛。城頭子路、刁子都眾十余萬人,流竄黃河、濟水之間;銅馬眾達數十萬,流竄於清陽;尤來、五幡流竄於山陽、射犬;再加上各郡縣豪傑的半割據武裝,要想徹底安定河北,難度可想而知。而這也就決定了,朝廷派往河北的人選,不僅級別要夠高,而且必須才幹非凡。
在綠林軍和南陽豪傑之中,無人願意接過河北這只燙手山芋。皇帝劉玄也想趁機培植自己的勢力,打算派壹名劉氏子弟前往,問計於大司徒劉賜。劉賜有意成全劉秀,於是答道:“劉氏子弟,只有劉秀可用。”
劉玄再問大司馬朱鮪:“寡人欲遣劉秀前往河北,大司馬意下如何?”朱鮪壹票否決,道:“劉秀壹到河北,必然謀反。”劉玄聞言,心中狐疑不安,再不提起這茬兒。
初,劉秀聽說劉玄有意派遣自己前往河北,暗中大喜,河北正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外放之地,地域廣袤,人口眾多,壹旦能收歸己有,足以爭霸天下。然而,朝廷任命卻久久不下,劉秀不免忐忑不安,向劉賜壹打聽,乃知朱鮪從中作梗,心中大恨。劉賜安慰劉秀道:“為今之計,當求告左丞相曹竟。”
曹竟,河北山陽人,儒生出身,漢朝舊吏,王莽篡漢之後,曹竟辭官歸鄉,拒食新朝俸祿,由此以忠義聞名天下。劉玄定都洛陽之後,征召曹竟入朝,拜為左丞相,以表勸忠良,號召天下。和劉賜相比,曹竟不僅資歷更深,威望更高,而且不帶派系色彩,由他出面替劉秀做說客,的確再合適不過。
劉秀官居司隸校尉,兼有洛陽房管局局長之權,當即批下條子,重賄曹竟豪宅壹處。曹竟大怒,斥劉秀道:“小子無狀!行此官場惡習!有事說來,老夫可為則為。老夫若不可為,縱賄我萬金,終不可為。”劉秀大慚,當即以願平定河北相告。曹竟這才轉怒為喜,熟視劉秀,道:“文叔昆陽壹戰,誠天下之奇跡。遍觀滿朝上下,堪能平定河北者,舍君其誰!今君主動請纓,實乃國家之幸,老夫自當為君保舉。”
曹竟見劉玄,道:“陛下可知臣之姓由何而來?”劉玄搖頭道:“不知。”曹竟道:“當年,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,建立曹國,其後人便以曹為姓,曹姓從此而來。”
劉玄書雖念得少,卻也看出曹竟絕非專為給他補習歷史課而來,於是說道:“老丞相有話直講,不必繞彎。”
曹竟道:“以老臣之見,周朝能有八百年江山,全靠封建同姓兄弟。漢朝傳國至今,中途雖有王莽篡位,最終猶能復興,也是因為廣封劉氏宗族的緣故。強秦二世而亡,罪在秦始皇立郡樹縣,嬴氏子弟無尺土之封。如今陛下登基未久,理當效法武王、高祖,廣樹同宗兄弟,分據要津,以為朝廷藩屏,守望互助,共衛漢室。河北乃天下重地,當以劉氏子弟鎮守,不可使異姓居之。今劉氏子弟之中,唯劉秀可定河北,願陛下遣之。”
劉玄聽罷,沈吟未決。曹竟知道劉玄對劉秀並不放心,於是又勸道:“綠林軍與南陽豪傑共殺劉秀長兄劉縯,劉秀能幸存至今,全賴陛下庇護之恩。今綠林軍與南陽豪傑把持朝政,有尾大不掉之勢。陛下遣劉秀安定河北,是為陛下樹壹強援也。萬壹日後朝中有變,劉秀愛陛下而恨綠林軍與南陽豪傑,只需陛下壹紙詔書,劉秀必率河北精兵,為陛下而戰。”
曹竟所言,正撓中劉玄癢處。劉玄名為皇帝,卻飽受綠林軍與南陽豪傑之掣肘,意誌不得自由,其勢有如傀儡。劉玄何嘗不想和綠林軍與南陽豪傑攤牌,然而苦於沒有自己的嫡系,只能壹忍再忍,不敢動手。劉秀是他的同宗兄弟,又與綠林軍和南陽豪傑有深仇大恨,很值得栽培成為嫡系,為日後攤牌早作準備。
劉玄主意已定,又對曹竟嘆道:“寡人雖欲遣文叔,大司馬卻不同意,為之奈何?”
曹竟答道:“陛下既已決斷,大司馬那邊,自有老臣。”
曹竟見大司馬朱鮪,劈頭便問:“大司馬欲廢皇帝乎?”
朱鮪大驚,慌忙辯解道:“我為漢臣,豈敢有不臣之心。”
曹竟再問道:“如此說來,天下仍是劉氏的天下?”
朱鮪只得答道:“高祖天下,自應為劉氏所有。”
曹竟氣勢更盛,又追問道:“自三代至於高祖,無不封建同姓,千年不易。今皇帝欲遣劉秀至河北,此乃劉氏家事,大司馬為何以疏間親,壹再阻攔?”
朱鮪急道:“劉秀心懷異誌,只恐壹到河北,便行謀反。”
曹竟怒道:“日後之事,雖聖人不敢妄斷。大司馬說劉秀將會造反,劉秀不能辯白。今有人說大司馬將會造反,大司馬能辯白乎?”
朱鮪理屈,不能答。
曹竟有如教訓小兒,繼續質問朱鮪道:“大司馬開國之功,較高祖功臣張良、韓信不遑多讓。大司馬也當自問,妳究竟是想做張良,還是要當韓信?”
朱鮪聞言,悚然而驚。劉邦得天下之後,張良甩手不幹,得以善終,韓信戀棧不去,終遭殺戮。朱鮪思之良久,茫然自失,跪謝曹竟道:“小子敬受教!劉秀之事,自應由皇帝決斷。”
朱鮪既已點頭,劉玄於是頒下詔書,命劉秀行大司馬事,持節北渡黃河,鎮慰河北州郡。至此,劉秀終於可以擺脫生命危險,如願離開洛陽。至此,劉秀也終於可以在心中惡狠狠地對自己說上壹句:“那些未能殺死我的,將使我更為堅強。”
【No.2 利涉大川】
《易》,“需”卦:“有孚,光亨,貞吉。利涉大川。”
十月將盡,萬物蕭瑟。孟津渡口,兩葉小舟緩緩劃入黃河,迎著波濤,向對岸奮力劃去。劉秀坐於當先的小舟,衣帶臨風,全身滾燙,以至於不得不將雙手浸於河水之中,尋求冰涼。手如刀,割開河水,分而輒合。
快樂,無與倫比的快樂,幾乎超越了他身體所能承受的極限,要將他炸為碎片。
換壹個人和劉秀易地而處,非但不會快樂,反而完全有理由感到沮喪。朱鮪之所以同意劉秀前往河北,壹來是聽了曹竟的勸誡,二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妥協。
朱鮪最忌憚的,莫過於日後劉秀要為他長兄劉縯復仇,不過仔細壹想,劉縯之死,他朱鮪固然是罪魁禍首,但皇帝劉玄的手上同樣有血,因此,劉縯之死已是鐵案,只要皇帝劉玄在位,便沒有人敢於翻案。既然無從翻案,劉秀也就無從復仇。萬壹劉秀到了河北,勢力坐大,開始謀反怎麽辦?對此,朱鮪也早有防備,妳劉秀去河北可以,但是朝廷壹不給兵,二不給錢,三不給糧。等到了河北,嗬,妳就自生自滅去吧。
劉秀自起兵以來,南征北戰,也攢下了不少嫡系部屬。然而,正是這些所謂的嫡系,聽說劉秀要錢沒錢,要糧沒糧,要兵沒兵,卻還要去河北赴湯蹈火,二次創業,紛紛打起了退堂鼓,百般借口推辭,不肯同行。放眼望去,不離不棄追隨劉秀前往河北的嫡系,只有眼前的馮異、銚期、王霸、祭遵、臧宮、堅鐔等二十余人而已,區區兩葉小舟載起來,都顯得綽綽有余。
除了馮異等人之外,劉秀的資本便只剩下朝廷的授權——行大司馬事,持節。授權聽上去很牛氣,然而全是虛的。手下壹兵壹卒也沒有,大司馬之事又從何行起?至於“節”,更只是壹根竹棍而已,柄長八尺,頭上束三重牦牛尾旄。知道的人,曉得這是代表皇帝親臨的權杖,不知道的人,還以為是丐幫的打狗棒呢。
而此行的目的地河北,也遠非流淌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,而是充斥著流民、豪傑、野心家,割據武裝,危機四伏,荊棘叢生。從洛陽到河北,劉秀可謂是才脫狼窟,又入虎穴。
盡管如此,劉秀的快樂依然不可阻擋。前路雖然艱難,但他再也不用忍辱偷生,仰人鼻息,他已經嘗夠了他人即地獄的滋味,無論他此行是成是敗,是生是死,至少這壹次,命運是掌握在他自己手裏。
船剛入水之時,劉秀心急如焚,恨不能身生雙翅,直接飛到河對岸去。待船行至黃河中心,劉秀這才漸漸平靜下來,他的脫逃終於已成定局,就算朱鮪突然反悔,現在也沒有辦法將他追回。
劉秀悠閑地看著老邁的艄公有節奏地劃著船槳,每劃下壹槳,他便遠離洛陽壹丈。壹群大雁掠空而過,劉秀目送雁群飛遠,嘴角按捺不住地微笑起來。大雁南飛,我將北行,各得其所,各安天命。
直至此時,劉秀方才有心情欣賞眼前的風景。這是他第壹次看見黃河,比他想象中的更為寬闊,水光連綿,幾乎壹直鋪至天邊,薄霧漸起,兩岸影影綽綽。隨行諸將大多和劉秀壹樣,也是第壹次見到黃河,大呼小叫,贊不絕口。
劉秀環視諸將,大笑道:“遙想當年,武王伐紂,正是自此渡河北上,牧野壹戰而滅商。如今,我們正走在當年武王的老路上。”
諸將見劉秀以周武王自比,無不心中暗喜。
小舟平安抵達對岸,劉秀重賞艄公。艄公大喜道:“待將軍南歸之日,老朽當再載將軍過河。”劉秀大笑道:“我若南歸,必領千軍萬馬,老人家的小舟,只怕是載不下了。”
艄公千恩萬謝,駕小舟回返。馮異等人身在異鄉為異客,皆有手足無措之感,紛紛望著劉秀。劉秀雖然只有二十九歲,卻已是他們無可爭議的領袖,他們像信徒信仰教主壹樣信仰他,像孩子依賴大人壹樣依賴他。
劉秀狠狠跺著腳下堅實的大地,向眾人大叫道:“腳下便是河北。潁川從我者多逝,而諸君獨留。疾風知勁草。努力!”眾人士氣大振,齊聲吶喊:“努力!”
劉秀眼望對岸的洛陽,久不出聲,如同壹尊凝固的雕像。忽然,劉秀擡起頭來,仰天號叫。他將他此前所有的委屈、憤怒、悲傷,悉數發泄在了這號叫之中。洛陽的劉玄、朱鮪等人,自然已經聽不見他的號叫,就算他們能夠聽見,劉秀也根本不在乎。
眾人閑極無聊,跟著劉秀壹道,向對岸放肆地號叫著。他們如同壹群逃出牢籠的野獸,邊號邊笑。他們的聲音,在這壹天響徹古老的黃河。
【No.3 圍爐夜話】
作為河北地區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,劉秀在河陽城外傳舍度過了他來河北之後的初夜。部下們經過壹日奔波,此刻皆已鼾聲如雷,劉秀卻了無睡意,獨自在廊外圍爐烤火。其時月明星稀,白霜鋪地,仰觀蒼穹無盡,靜聽四野空寂。劉秀坐於異鄉深沈的夜,未來不可預期,而鄉愁悄然來襲。
去年此時,他和長兄劉縯共同起兵,誓要推翻王莽,光復漢室。壹年之後,既定目標完成,但是經歷了怎樣的過程!他先後失去了母親、二哥、二姐,而本應成為皇帝的長兄劉縯,更是在壹場權力內訌中犧牲。盡管他個人在這壹年收獲頗豐,先是指揮了震驚天下的昆陽大戰,後來又迎娶了自己的夢中情人,然而這些成就卻遠不足以洗刷他內心深處的悲傷和恥辱。如今,他更流落河北——壹個他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,等待他的,將是陌生的人們、叵測的命運。
劉秀正惆悵自傷,身後忽有腳步聲傳來,回頭壹看,乃是馮異。馮異見過劉秀,問道:“明公已至河北,敢問安撫方略。”劉秀道:“以君之見,該當如何?”
馮異答道:“今綠林諸將縱橫恣意,所到之處,搶占婦女,擄掠財物。劉玄雖為漢帝,百姓卻並不擁戴。有桀紂之亂,乃見湯武之功;民之饑渴,易為飲食時也。今公專命方面,宜急分遣官屬,理冤結,施恩惠。”
劉秀笑道:“公孫之見,正與我合。”
馮異遲疑片刻,又道:“異有壹言,不知當講不當講。”劉秀道:“但講無妨。”
馮異伏地言道:“明公兄弟二人,首舉義兵,天下歸心。漢帝之位,本歸伯升,伯升死,則歸明公。劉玄竊位,伯升蒙難,天下多冤之。如今天助明公,使明公安集河北。河北地廣人眾,資財富饒,堪為龍興之地。明公得河北,則天下可圖,願深思之。”
劉秀面色壹沈,我這才剛到河北,壹兵未收,寸地未得,妳馮異就慫恿我伺機造反,也實在太不淡定了吧!當即斥道:“國法無情,卿勿妄言!”
兩日後,劉秀行至河內郡治懷縣。河內太守韓歆見長官駕到,不敢怠慢,置酒相迎。劉秀初到異地,本以為舉目無親,忽在席間發現岑彭,心中大驚。酒罷席散,劉秀歸驛館,前腳進門,後腳便報岑彭來訪。
劉秀迎入岑彭,問道:“聞岑兄官拜潁川太守,何以竟在此地逗留?”岑彭苦笑道:“我雖欲到潁川赴任,無奈君家族叔劉茂不答應!”
劉茂,出身舂陵劉氏,年僅十八,但論起輩分來,卻是劉秀的族叔。劉秀兄弟起兵之時,劉茂也同時在河南郡起兵,自號劉失職,稱厭新將軍,先後攻下潁川、汝南,麾下眾十余萬人。
岑彭當年為新朝死守宛城,城中人相食,這才投降漢軍,眾人皆欲殺,劉縯愛惜岑彭之才,特加赦免,收為部屬。劉縯遇害之後,岑彭歸於大司馬朱鮪,屢立戰功,官拜潁川太守。
割據潁川、汝南二郡的劉茂,自恃乃劉玄族叔,根本不把劉玄的更始朝廷放在眼裏。岑彭剛入潁川,立即遭到劉茂武力驅逐。岑彭不能到任,也無顏再回朝廷復命,只得率部屬百余人投奔河內太守韓歆。
劉秀聽完岑彭的遭遇,嘆息不已。岑彭見左右無人,私語劉秀道:“岑某之命,全拜伯升所賜。本欲輔佐伯升,定鼎天下,無奈伯升早死,不得為用,至今引以為恨。今見文叔,如見伯升,願以身自效,以報伯升當日救命之恩。”
見岑彭有意追隨自己,劉秀不明真假,婉拒道:“岑兄乃大司馬朱鮪之愛將,我豈敢橫刀奪愛。”
岑彭見劉秀心存疑慮,壹時也不能自辯,於是又道:“河北為王者之地,得之可成霸業,還望文叔多加留意。河內太守韓歆,乃岑某故人,對岑某言聽計從。文叔南歸之日,岑某必命韓歆舉河內而降,為文叔先驅。”
馮異身為劉秀親信,提及造反,劉秀尚且不敢貿然答應,更何況岑彭乃是朱鮪部下,卻也來慫恿劉秀造反,劉秀自然越發警惕,當即道:“妳我皆為漢臣,理當盡忠竭力,共扶漢室。此等大逆不道語,休再提起!”
次日,劉秀辭別河內,向邯鄲進發。壹路慰勉官吏,撫循百姓,理結冤案,廢除苛政。所到之處,吏民無不歡喜,夾道相迎,爭獻牛酒,劉秀皆辭而不受。
數日之後,劉秀行至鄴縣,時已日暮,正欲投宿,忽聞身後大呼:“劉文叔休走!”
【No.4 鄴城獻策】
且說劉秀等人行至鄴縣,忽聞身後壹聲大喊,不由大驚,以為是大部隊前來追襲,急忙勒馬,回首望去,卻見來者只是壹位年輕儒生,正拄著拐杖從遠處徐徐走來。眾人尚未看清儒生面目,劉秀卻已拊掌大笑,道:“此必鄧禹鄧仲華是也。”
儒生邁著碎步,緊趕慢趕,終於將面部和身體壹並呈現在眾人眼前,正是劉秀當年同窗,十三歲便入太學的神童鄧禹。劉秀打量著鄧禹,但見昔日幼童,已長成二十二歲的俊俏青年,當年六尺之軀,如今居然偉岸;舊日鼻涕流處,壹捧疑似美髯。劉秀越看越樂,問鄧禹道:“自新野而來?”鄧禹點頭道:“是。”劉秀笑道:“小子孤身壹人,千裏橫行,壯哉!”
劉秀趕路之際,不便細談,當即為鄧禹壹壹引見,然後率眾入鄴城不提。夜半,劉秀召見鄧禹,笑問道:“我專命河北,可以隨意封官拜將。妳千裏而來,莫非是為了求個壹官半職?”
鄧禹恭謹答道:“禹之來,不求做官。”
劉秀道:“那妳求什麽?”
鄧禹道:“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,禹得效其尺寸,垂功名於竹帛耳。”
劉秀大笑,道:“皇帝劉玄征妳入朝為官,妳屢次拒絕。如今我孤懸河北,妳卻主動前來投奔。何故?”
鄧禹道:“只為妳當年的壹句話。”
劉秀壹楞,問道:“哪句話?”
鄧禹道:“大江!滄海!”
劉秀嗟嘆久之,笑道:“當年戲言,不意妳竟當真。”
鄧禹搖搖頭,意味深長地答道:“君無戲言!”
劉秀大驚,鄧禹和他多年不見,壹見面怎麽就跟馮異和岑彭壹樣,也要慫恿他造反當皇帝?於是佯怒道:“此話從何說起?”
鄧禹道:“‘狂風拔倒樹,樹倒根已露。上有數枝藤,青青猶未悟’,明公聽過此詩乎?”
劉秀笑道:“妳忽然提及此詩,可有說法沒有?”
鄧禹道:“劉玄,樹也。劉玄之樹將倒矣。劉玄雖已稱帝,而天下之亂方起。山東赤眉、青犢之屬,動以萬數,三輔盜賊,往往群聚。劉玄名為皇帝,實為諸將所挾持,有心無力,而諸將皆庸人暴起,誌在財幣,爭用威力,朝夕自快而已,非有忠良明智,深慮遠圖,欲尊主安民者也。四方分崩離析,形勢可見!”
鄧禹再道:“公,藤也。劉玄之樹既倒,公雖能安定河北,建藩輔之功,猶恐無所成立,不足為長久之計。”
劉秀笑望鄧禹,像長輩望著正在表演的孩子,道:“說下去!”
鄧禹道:“聖人不得違時,時亦不可失也。劉玄既是庸才,不足以擔當帝王大業,自應有聖人取而代之。公初戰昆陽,破王莽百萬之眾,天下聞知,莫不震靡,此公之武功也。公推誠接士,少長有禮,賞善如不及,討惡如慮遙,此公之文治也。文治武功集於壹身,所謂天下聖人也。於今之計,莫過於應民之望,延攬英雄,務悅民心。以公之威德,立高祖之業,救萬民之命,此其時矣!”
劉秀笑道:“我無遠慮,只有近憂。天下非所敢望,可有定河北之策?”
鄧禹道:“河北定,則天下自定。河內被山帶河,足以為固,其土地富貴,殷之舊都,公之有此,猶高祖之有關中也。既得河內,再進兵定冀州,北取幽州、並州,得胡馬之用;東舉青州、徐州,引負海之利。河北已平,五州既集,南面以號令,天下如在囊中,探手可取也。”
鄧禹寥寥數語,天下事仿佛已盡在掌握。後人稱此為“鄴城策”,與諸葛亮“隆中對”同為“秀才不出門,便知天下事”之典範。劉秀聽罷,嘆賞道:“小兒,昔日張良乎?”
鄧禹拜伏於地,恭聲道:“明公,今日高祖也。”
兩人相視大笑,當夜聯床抵足,敘舊竟夜,不勝歡暢。
自此之後,劉秀號鄧禹為鄧將軍,特加親近,常令同宿,相與計議。又授鄧禹以人事大權,命其考察諸將,薦舉人才。
鄧禹如此年輕,又是初來乍到,權位卻淩駕於眾人之上,眾人不免將信將疑,很是擔心劉秀的眼力。劉秀曉諭眾人道:“世間有三歲老翁,也有百歲兒童。我初識鄧禹之時,鄧禹年僅十三,卻已經老成持重,非常人可及。諸君未可輕年少,宣父猶能畏後生。鄧禹之能,他日必顯。”
這段禱詞寫在下面:
“我們在天上的父,我們日用的飲食,今日賜給我們。免我們的債,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,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,全是妳的,直到永遠。”
漢更始元年(公元二十三年)十月,洛陽。劉秀的處境相當不妙,他的債無法免去,他遇見的試探無處不在,而又有誰能救他脫離兇惡?
劉秀所能做的,似乎只剩下祈禱而已。
洛陽城中,血光正在醞釀,朱鮪等人已經為他伏下刀槍。這不僅是他的預感,更有劉賜的提醒為證。倘若他只想保命,事情倒也簡單,大不了改換姓名,亡命他鄉,萬人海中壹身藏,從此山林中多了壹位蕭索的隱士,又或者村莊裏多了壹位卑微的農夫,而世間不再有劉秀劉文叔。然而,像這樣壹躲,他雖然能活下去,卻無異於已經死了,他的仇恨、雄心,包括與陰麗華的婚姻,隨著這壹躲,將從此無聲飲恨,化為無人過問的小徑,荒草長滿,抱憾殘生。
因此,他不僅要活下去,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活下去。他的確要遠離洛陽,躲離朱鮪等人的魔掌,但絕不能以逃亡的方式,而必須以漢朝官員的身份堂堂正正地離開,外放到壹個天高皇帝遠、可以積攢實力的地方。
而就漢朝更始政府而言,盡管王莽的新朝已經覆滅,但天下並不太平,全國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州郡並未正式納入帝國的版圖,因此也就需要大量的外放官員,前往這些州郡進行安撫招降。
更始政府中的當權派——出身綠林軍和南陽豪傑的那些高級將領們,沒有人願意外放,他們明白,很快就要大賞功臣,瓜分勝利果實,在此關鍵時刻,他們都爭著要留在皇帝劉玄身邊,盯緊自己該得的那份封賞。因此,安撫州郡的任務,很自然地便落在了壹批低級官吏的頭上。
在眾多尚未歸順朝廷的州郡之中,河北地區是壹個例外。所謂河北,在當時泛指黃河以北,地域涵蓋今之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地。其余州郡,即使派壹個不得力的低級官吏去,也可以傳檄而定。然而在河北,局面卻遠非如此輕易。
河北地區乃戰國時代的燕趙故地,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,民風強悍,野心家眾多,而此時的河北,更是流民武裝滋盛。城頭子路、刁子都眾十余萬人,流竄黃河、濟水之間;銅馬眾達數十萬,流竄於清陽;尤來、五幡流竄於山陽、射犬;再加上各郡縣豪傑的半割據武裝,要想徹底安定河北,難度可想而知。而這也就決定了,朝廷派往河北的人選,不僅級別要夠高,而且必須才幹非凡。
在綠林軍和南陽豪傑之中,無人願意接過河北這只燙手山芋。皇帝劉玄也想趁機培植自己的勢力,打算派壹名劉氏子弟前往,問計於大司徒劉賜。劉賜有意成全劉秀,於是答道:“劉氏子弟,只有劉秀可用。”
劉玄再問大司馬朱鮪:“寡人欲遣劉秀前往河北,大司馬意下如何?”朱鮪壹票否決,道:“劉秀壹到河北,必然謀反。”劉玄聞言,心中狐疑不安,再不提起這茬兒。
初,劉秀聽說劉玄有意派遣自己前往河北,暗中大喜,河北正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外放之地,地域廣袤,人口眾多,壹旦能收歸己有,足以爭霸天下。然而,朝廷任命卻久久不下,劉秀不免忐忑不安,向劉賜壹打聽,乃知朱鮪從中作梗,心中大恨。劉賜安慰劉秀道:“為今之計,當求告左丞相曹竟。”
曹竟,河北山陽人,儒生出身,漢朝舊吏,王莽篡漢之後,曹竟辭官歸鄉,拒食新朝俸祿,由此以忠義聞名天下。劉玄定都洛陽之後,征召曹竟入朝,拜為左丞相,以表勸忠良,號召天下。和劉賜相比,曹竟不僅資歷更深,威望更高,而且不帶派系色彩,由他出面替劉秀做說客,的確再合適不過。
劉秀官居司隸校尉,兼有洛陽房管局局長之權,當即批下條子,重賄曹竟豪宅壹處。曹竟大怒,斥劉秀道:“小子無狀!行此官場惡習!有事說來,老夫可為則為。老夫若不可為,縱賄我萬金,終不可為。”劉秀大慚,當即以願平定河北相告。曹竟這才轉怒為喜,熟視劉秀,道:“文叔昆陽壹戰,誠天下之奇跡。遍觀滿朝上下,堪能平定河北者,舍君其誰!今君主動請纓,實乃國家之幸,老夫自當為君保舉。”
曹竟見劉玄,道:“陛下可知臣之姓由何而來?”劉玄搖頭道:“不知。”曹竟道:“當年,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,建立曹國,其後人便以曹為姓,曹姓從此而來。”
劉玄書雖念得少,卻也看出曹竟絕非專為給他補習歷史課而來,於是說道:“老丞相有話直講,不必繞彎。”
曹竟道:“以老臣之見,周朝能有八百年江山,全靠封建同姓兄弟。漢朝傳國至今,中途雖有王莽篡位,最終猶能復興,也是因為廣封劉氏宗族的緣故。強秦二世而亡,罪在秦始皇立郡樹縣,嬴氏子弟無尺土之封。如今陛下登基未久,理當效法武王、高祖,廣樹同宗兄弟,分據要津,以為朝廷藩屏,守望互助,共衛漢室。河北乃天下重地,當以劉氏子弟鎮守,不可使異姓居之。今劉氏子弟之中,唯劉秀可定河北,願陛下遣之。”
劉玄聽罷,沈吟未決。曹竟知道劉玄對劉秀並不放心,於是又勸道:“綠林軍與南陽豪傑共殺劉秀長兄劉縯,劉秀能幸存至今,全賴陛下庇護之恩。今綠林軍與南陽豪傑把持朝政,有尾大不掉之勢。陛下遣劉秀安定河北,是為陛下樹壹強援也。萬壹日後朝中有變,劉秀愛陛下而恨綠林軍與南陽豪傑,只需陛下壹紙詔書,劉秀必率河北精兵,為陛下而戰。”
曹竟所言,正撓中劉玄癢處。劉玄名為皇帝,卻飽受綠林軍與南陽豪傑之掣肘,意誌不得自由,其勢有如傀儡。劉玄何嘗不想和綠林軍與南陽豪傑攤牌,然而苦於沒有自己的嫡系,只能壹忍再忍,不敢動手。劉秀是他的同宗兄弟,又與綠林軍和南陽豪傑有深仇大恨,很值得栽培成為嫡系,為日後攤牌早作準備。
劉玄主意已定,又對曹竟嘆道:“寡人雖欲遣文叔,大司馬卻不同意,為之奈何?”
曹竟答道:“陛下既已決斷,大司馬那邊,自有老臣。”
曹竟見大司馬朱鮪,劈頭便問:“大司馬欲廢皇帝乎?”
朱鮪大驚,慌忙辯解道:“我為漢臣,豈敢有不臣之心。”
曹竟再問道:“如此說來,天下仍是劉氏的天下?”
朱鮪只得答道:“高祖天下,自應為劉氏所有。”
曹竟氣勢更盛,又追問道:“自三代至於高祖,無不封建同姓,千年不易。今皇帝欲遣劉秀至河北,此乃劉氏家事,大司馬為何以疏間親,壹再阻攔?”
朱鮪急道:“劉秀心懷異誌,只恐壹到河北,便行謀反。”
曹竟怒道:“日後之事,雖聖人不敢妄斷。大司馬說劉秀將會造反,劉秀不能辯白。今有人說大司馬將會造反,大司馬能辯白乎?”
朱鮪理屈,不能答。
曹竟有如教訓小兒,繼續質問朱鮪道:“大司馬開國之功,較高祖功臣張良、韓信不遑多讓。大司馬也當自問,妳究竟是想做張良,還是要當韓信?”
朱鮪聞言,悚然而驚。劉邦得天下之後,張良甩手不幹,得以善終,韓信戀棧不去,終遭殺戮。朱鮪思之良久,茫然自失,跪謝曹竟道:“小子敬受教!劉秀之事,自應由皇帝決斷。”
朱鮪既已點頭,劉玄於是頒下詔書,命劉秀行大司馬事,持節北渡黃河,鎮慰河北州郡。至此,劉秀終於可以擺脫生命危險,如願離開洛陽。至此,劉秀也終於可以在心中惡狠狠地對自己說上壹句:“那些未能殺死我的,將使我更為堅強。”
【No.2 利涉大川】
《易》,“需”卦:“有孚,光亨,貞吉。利涉大川。”
十月將盡,萬物蕭瑟。孟津渡口,兩葉小舟緩緩劃入黃河,迎著波濤,向對岸奮力劃去。劉秀坐於當先的小舟,衣帶臨風,全身滾燙,以至於不得不將雙手浸於河水之中,尋求冰涼。手如刀,割開河水,分而輒合。
快樂,無與倫比的快樂,幾乎超越了他身體所能承受的極限,要將他炸為碎片。
換壹個人和劉秀易地而處,非但不會快樂,反而完全有理由感到沮喪。朱鮪之所以同意劉秀前往河北,壹來是聽了曹竟的勸誡,二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妥協。
朱鮪最忌憚的,莫過於日後劉秀要為他長兄劉縯復仇,不過仔細壹想,劉縯之死,他朱鮪固然是罪魁禍首,但皇帝劉玄的手上同樣有血,因此,劉縯之死已是鐵案,只要皇帝劉玄在位,便沒有人敢於翻案。既然無從翻案,劉秀也就無從復仇。萬壹劉秀到了河北,勢力坐大,開始謀反怎麽辦?對此,朱鮪也早有防備,妳劉秀去河北可以,但是朝廷壹不給兵,二不給錢,三不給糧。等到了河北,嗬,妳就自生自滅去吧。
劉秀自起兵以來,南征北戰,也攢下了不少嫡系部屬。然而,正是這些所謂的嫡系,聽說劉秀要錢沒錢,要糧沒糧,要兵沒兵,卻還要去河北赴湯蹈火,二次創業,紛紛打起了退堂鼓,百般借口推辭,不肯同行。放眼望去,不離不棄追隨劉秀前往河北的嫡系,只有眼前的馮異、銚期、王霸、祭遵、臧宮、堅鐔等二十余人而已,區區兩葉小舟載起來,都顯得綽綽有余。
除了馮異等人之外,劉秀的資本便只剩下朝廷的授權——行大司馬事,持節。授權聽上去很牛氣,然而全是虛的。手下壹兵壹卒也沒有,大司馬之事又從何行起?至於“節”,更只是壹根竹棍而已,柄長八尺,頭上束三重牦牛尾旄。知道的人,曉得這是代表皇帝親臨的權杖,不知道的人,還以為是丐幫的打狗棒呢。
而此行的目的地河北,也遠非流淌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,而是充斥著流民、豪傑、野心家,割據武裝,危機四伏,荊棘叢生。從洛陽到河北,劉秀可謂是才脫狼窟,又入虎穴。
盡管如此,劉秀的快樂依然不可阻擋。前路雖然艱難,但他再也不用忍辱偷生,仰人鼻息,他已經嘗夠了他人即地獄的滋味,無論他此行是成是敗,是生是死,至少這壹次,命運是掌握在他自己手裏。
船剛入水之時,劉秀心急如焚,恨不能身生雙翅,直接飛到河對岸去。待船行至黃河中心,劉秀這才漸漸平靜下來,他的脫逃終於已成定局,就算朱鮪突然反悔,現在也沒有辦法將他追回。
劉秀悠閑地看著老邁的艄公有節奏地劃著船槳,每劃下壹槳,他便遠離洛陽壹丈。壹群大雁掠空而過,劉秀目送雁群飛遠,嘴角按捺不住地微笑起來。大雁南飛,我將北行,各得其所,各安天命。
直至此時,劉秀方才有心情欣賞眼前的風景。這是他第壹次看見黃河,比他想象中的更為寬闊,水光連綿,幾乎壹直鋪至天邊,薄霧漸起,兩岸影影綽綽。隨行諸將大多和劉秀壹樣,也是第壹次見到黃河,大呼小叫,贊不絕口。
劉秀環視諸將,大笑道:“遙想當年,武王伐紂,正是自此渡河北上,牧野壹戰而滅商。如今,我們正走在當年武王的老路上。”
諸將見劉秀以周武王自比,無不心中暗喜。
小舟平安抵達對岸,劉秀重賞艄公。艄公大喜道:“待將軍南歸之日,老朽當再載將軍過河。”劉秀大笑道:“我若南歸,必領千軍萬馬,老人家的小舟,只怕是載不下了。”
艄公千恩萬謝,駕小舟回返。馮異等人身在異鄉為異客,皆有手足無措之感,紛紛望著劉秀。劉秀雖然只有二十九歲,卻已是他們無可爭議的領袖,他們像信徒信仰教主壹樣信仰他,像孩子依賴大人壹樣依賴他。
劉秀狠狠跺著腳下堅實的大地,向眾人大叫道:“腳下便是河北。潁川從我者多逝,而諸君獨留。疾風知勁草。努力!”眾人士氣大振,齊聲吶喊:“努力!”
劉秀眼望對岸的洛陽,久不出聲,如同壹尊凝固的雕像。忽然,劉秀擡起頭來,仰天號叫。他將他此前所有的委屈、憤怒、悲傷,悉數發泄在了這號叫之中。洛陽的劉玄、朱鮪等人,自然已經聽不見他的號叫,就算他們能夠聽見,劉秀也根本不在乎。
眾人閑極無聊,跟著劉秀壹道,向對岸放肆地號叫著。他們如同壹群逃出牢籠的野獸,邊號邊笑。他們的聲音,在這壹天響徹古老的黃河。
【No.3 圍爐夜話】
作為河北地區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,劉秀在河陽城外傳舍度過了他來河北之後的初夜。部下們經過壹日奔波,此刻皆已鼾聲如雷,劉秀卻了無睡意,獨自在廊外圍爐烤火。其時月明星稀,白霜鋪地,仰觀蒼穹無盡,靜聽四野空寂。劉秀坐於異鄉深沈的夜,未來不可預期,而鄉愁悄然來襲。
去年此時,他和長兄劉縯共同起兵,誓要推翻王莽,光復漢室。壹年之後,既定目標完成,但是經歷了怎樣的過程!他先後失去了母親、二哥、二姐,而本應成為皇帝的長兄劉縯,更是在壹場權力內訌中犧牲。盡管他個人在這壹年收獲頗豐,先是指揮了震驚天下的昆陽大戰,後來又迎娶了自己的夢中情人,然而這些成就卻遠不足以洗刷他內心深處的悲傷和恥辱。如今,他更流落河北——壹個他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,等待他的,將是陌生的人們、叵測的命運。
劉秀正惆悵自傷,身後忽有腳步聲傳來,回頭壹看,乃是馮異。馮異見過劉秀,問道:“明公已至河北,敢問安撫方略。”劉秀道:“以君之見,該當如何?”
馮異答道:“今綠林諸將縱橫恣意,所到之處,搶占婦女,擄掠財物。劉玄雖為漢帝,百姓卻並不擁戴。有桀紂之亂,乃見湯武之功;民之饑渴,易為飲食時也。今公專命方面,宜急分遣官屬,理冤結,施恩惠。”
劉秀笑道:“公孫之見,正與我合。”
馮異遲疑片刻,又道:“異有壹言,不知當講不當講。”劉秀道:“但講無妨。”
馮異伏地言道:“明公兄弟二人,首舉義兵,天下歸心。漢帝之位,本歸伯升,伯升死,則歸明公。劉玄竊位,伯升蒙難,天下多冤之。如今天助明公,使明公安集河北。河北地廣人眾,資財富饒,堪為龍興之地。明公得河北,則天下可圖,願深思之。”
劉秀面色壹沈,我這才剛到河北,壹兵未收,寸地未得,妳馮異就慫恿我伺機造反,也實在太不淡定了吧!當即斥道:“國法無情,卿勿妄言!”
兩日後,劉秀行至河內郡治懷縣。河內太守韓歆見長官駕到,不敢怠慢,置酒相迎。劉秀初到異地,本以為舉目無親,忽在席間發現岑彭,心中大驚。酒罷席散,劉秀歸驛館,前腳進門,後腳便報岑彭來訪。
劉秀迎入岑彭,問道:“聞岑兄官拜潁川太守,何以竟在此地逗留?”岑彭苦笑道:“我雖欲到潁川赴任,無奈君家族叔劉茂不答應!”
劉茂,出身舂陵劉氏,年僅十八,但論起輩分來,卻是劉秀的族叔。劉秀兄弟起兵之時,劉茂也同時在河南郡起兵,自號劉失職,稱厭新將軍,先後攻下潁川、汝南,麾下眾十余萬人。
岑彭當年為新朝死守宛城,城中人相食,這才投降漢軍,眾人皆欲殺,劉縯愛惜岑彭之才,特加赦免,收為部屬。劉縯遇害之後,岑彭歸於大司馬朱鮪,屢立戰功,官拜潁川太守。
割據潁川、汝南二郡的劉茂,自恃乃劉玄族叔,根本不把劉玄的更始朝廷放在眼裏。岑彭剛入潁川,立即遭到劉茂武力驅逐。岑彭不能到任,也無顏再回朝廷復命,只得率部屬百余人投奔河內太守韓歆。
劉秀聽完岑彭的遭遇,嘆息不已。岑彭見左右無人,私語劉秀道:“岑某之命,全拜伯升所賜。本欲輔佐伯升,定鼎天下,無奈伯升早死,不得為用,至今引以為恨。今見文叔,如見伯升,願以身自效,以報伯升當日救命之恩。”
見岑彭有意追隨自己,劉秀不明真假,婉拒道:“岑兄乃大司馬朱鮪之愛將,我豈敢橫刀奪愛。”
岑彭見劉秀心存疑慮,壹時也不能自辯,於是又道:“河北為王者之地,得之可成霸業,還望文叔多加留意。河內太守韓歆,乃岑某故人,對岑某言聽計從。文叔南歸之日,岑某必命韓歆舉河內而降,為文叔先驅。”
馮異身為劉秀親信,提及造反,劉秀尚且不敢貿然答應,更何況岑彭乃是朱鮪部下,卻也來慫恿劉秀造反,劉秀自然越發警惕,當即道:“妳我皆為漢臣,理當盡忠竭力,共扶漢室。此等大逆不道語,休再提起!”
次日,劉秀辭別河內,向邯鄲進發。壹路慰勉官吏,撫循百姓,理結冤案,廢除苛政。所到之處,吏民無不歡喜,夾道相迎,爭獻牛酒,劉秀皆辭而不受。
數日之後,劉秀行至鄴縣,時已日暮,正欲投宿,忽聞身後大呼:“劉文叔休走!”
【No.4 鄴城獻策】
且說劉秀等人行至鄴縣,忽聞身後壹聲大喊,不由大驚,以為是大部隊前來追襲,急忙勒馬,回首望去,卻見來者只是壹位年輕儒生,正拄著拐杖從遠處徐徐走來。眾人尚未看清儒生面目,劉秀卻已拊掌大笑,道:“此必鄧禹鄧仲華是也。”
儒生邁著碎步,緊趕慢趕,終於將面部和身體壹並呈現在眾人眼前,正是劉秀當年同窗,十三歲便入太學的神童鄧禹。劉秀打量著鄧禹,但見昔日幼童,已長成二十二歲的俊俏青年,當年六尺之軀,如今居然偉岸;舊日鼻涕流處,壹捧疑似美髯。劉秀越看越樂,問鄧禹道:“自新野而來?”鄧禹點頭道:“是。”劉秀笑道:“小子孤身壹人,千裏橫行,壯哉!”
劉秀趕路之際,不便細談,當即為鄧禹壹壹引見,然後率眾入鄴城不提。夜半,劉秀召見鄧禹,笑問道:“我專命河北,可以隨意封官拜將。妳千裏而來,莫非是為了求個壹官半職?”
鄧禹恭謹答道:“禹之來,不求做官。”
劉秀道:“那妳求什麽?”
鄧禹道:“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,禹得效其尺寸,垂功名於竹帛耳。”
劉秀大笑,道:“皇帝劉玄征妳入朝為官,妳屢次拒絕。如今我孤懸河北,妳卻主動前來投奔。何故?”
鄧禹道:“只為妳當年的壹句話。”
劉秀壹楞,問道:“哪句話?”
鄧禹道:“大江!滄海!”
劉秀嗟嘆久之,笑道:“當年戲言,不意妳竟當真。”
鄧禹搖搖頭,意味深長地答道:“君無戲言!”
劉秀大驚,鄧禹和他多年不見,壹見面怎麽就跟馮異和岑彭壹樣,也要慫恿他造反當皇帝?於是佯怒道:“此話從何說起?”
鄧禹道:“‘狂風拔倒樹,樹倒根已露。上有數枝藤,青青猶未悟’,明公聽過此詩乎?”
劉秀笑道:“妳忽然提及此詩,可有說法沒有?”
鄧禹道:“劉玄,樹也。劉玄之樹將倒矣。劉玄雖已稱帝,而天下之亂方起。山東赤眉、青犢之屬,動以萬數,三輔盜賊,往往群聚。劉玄名為皇帝,實為諸將所挾持,有心無力,而諸將皆庸人暴起,誌在財幣,爭用威力,朝夕自快而已,非有忠良明智,深慮遠圖,欲尊主安民者也。四方分崩離析,形勢可見!”
鄧禹再道:“公,藤也。劉玄之樹既倒,公雖能安定河北,建藩輔之功,猶恐無所成立,不足為長久之計。”
劉秀笑望鄧禹,像長輩望著正在表演的孩子,道:“說下去!”
鄧禹道:“聖人不得違時,時亦不可失也。劉玄既是庸才,不足以擔當帝王大業,自應有聖人取而代之。公初戰昆陽,破王莽百萬之眾,天下聞知,莫不震靡,此公之武功也。公推誠接士,少長有禮,賞善如不及,討惡如慮遙,此公之文治也。文治武功集於壹身,所謂天下聖人也。於今之計,莫過於應民之望,延攬英雄,務悅民心。以公之威德,立高祖之業,救萬民之命,此其時矣!”
劉秀笑道:“我無遠慮,只有近憂。天下非所敢望,可有定河北之策?”
鄧禹道:“河北定,則天下自定。河內被山帶河,足以為固,其土地富貴,殷之舊都,公之有此,猶高祖之有關中也。既得河內,再進兵定冀州,北取幽州、並州,得胡馬之用;東舉青州、徐州,引負海之利。河北已平,五州既集,南面以號令,天下如在囊中,探手可取也。”
鄧禹寥寥數語,天下事仿佛已盡在掌握。後人稱此為“鄴城策”,與諸葛亮“隆中對”同為“秀才不出門,便知天下事”之典範。劉秀聽罷,嘆賞道:“小兒,昔日張良乎?”
鄧禹拜伏於地,恭聲道:“明公,今日高祖也。”
兩人相視大笑,當夜聯床抵足,敘舊竟夜,不勝歡暢。
自此之後,劉秀號鄧禹為鄧將軍,特加親近,常令同宿,相與計議。又授鄧禹以人事大權,命其考察諸將,薦舉人才。
鄧禹如此年輕,又是初來乍到,權位卻淩駕於眾人之上,眾人不免將信將疑,很是擔心劉秀的眼力。劉秀曉諭眾人道:“世間有三歲老翁,也有百歲兒童。我初識鄧禹之時,鄧禹年僅十三,卻已經老成持重,非常人可及。諸君未可輕年少,宣父猶能畏後生。鄧禹之能,他日必顯。”